阅读:0
听报道
在大部分人眼里,管理的任务是一个完全不用讨论的词汇。身处组织之中,就必然要通过管理来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因此,才会有管理学者说“管理要对运营负责”。在历史长河中,管理一直被作为工具进行讨论,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从《管理的精神》一文开始,我们希望通过把有关“人”的内容赋予这个人们眼中的“工具”,让管理以思想的形态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
事实也足以证明,管理概念的缘起本就是思想成果的延续,它身上肩负的使命远不是“把人组织到一起”这么简单。管理更像是德鲁克寻求欧洲自救之路的方法,其背后的价值观是一套有待后人陆续完善的“知识观”。
我们在考察近一个世纪的商业史时发现,促发“管理”成为显学的,除了出现在美国的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和福特流水线,另一支力量绝不可被忽视。它几乎和美国开启大规模工业之路处于相同的时间点,它来源于思想界对欧洲这个人类的灾难中心的深度反思。
因为民主的传统差异,欧洲的反思也许并不适合美国,但它成为了人们在内心深处警惕极权、警惕混乱的非理性时代的闸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美剧、好莱坞电影这些传播流行文化的媒介,看到其背后的欧洲思想的力量。
管理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管理,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如果我们知道它之于社会会是怎样的,相应地,也就会知道针对组织,我们该如何对管理定位。但首先,它绝不是工具。
作为乌托邦的组织
关于社会管理这门学科,一位狂热的支持者曾这么写道:“当今这个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像五十年前技术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样。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很可能就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我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的时代。
以上这段话来自于阿道斯·赫胥黎所著的《重返美丽新世界》。和那本知名的小说不同,赫胥黎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地道的社会学论著。他从人口膨胀和科技肆无忌惮的发展导致的过度组织化出发,认为我们正在义无返顾地向着依赖独裁和精密控制搭建起的“美丽新世界”进发。
“美丽”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在墨索里尼统治期间,意大利的妇人们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啊,生活秩序井井有条,每个人在一个统一指令下各司其职。火车不再晚点,主要街道上看不到乞丐,意大利拥有南大西洋最快的轮船和最宽的马路。意大利的妇人们还嘲笑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你们有大萧条,我们没有。你们无法一下子动员几百万人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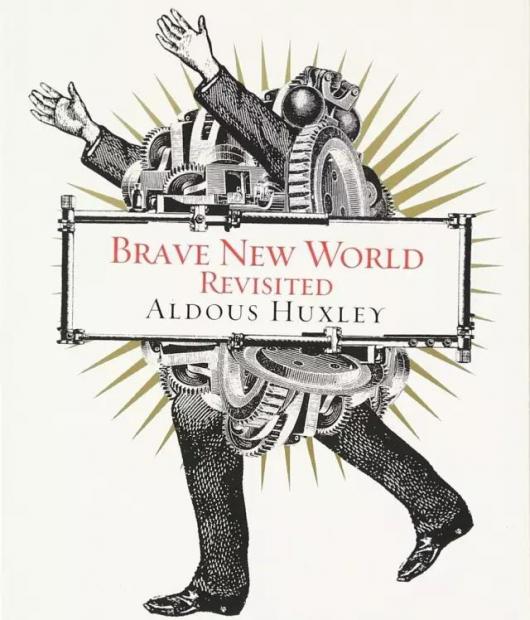
阿道司·赫胥黎于1958年完成《重返美丽新世界》的书稿
德鲁克说,这就是极权社会的“优势”,把原子论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看不到新秩序的崛起,却看到了旧秩序的衰亡。他们无能为力,却又不得不相信着自己本不相信的东西。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被各种洗脑术统一起来的恶魔机器。
就像赫胥黎批判的,“人口过剩、组织膨胀这两股冷酷的势力,以及想控制它们的社会工程师们,一起驱赶着我们走入一个新的中世纪体系,这回魂的幽灵世界或许比其前身更加合人心意,因为它会充斥《美丽新世界》里提供的种种赏心悦目之物,比如婴儿驯化、睡眠教育、嗑药快感;但是,对于大部分男男女女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奴役。”
赫胥黎对乌托邦的态度是极其悲观的,他认为当独裁者具备了科学能力之后,极权社会将完全无解。即使是教育也无能为力。为此,他还讽刺了霍桑实验的发起人埃尔顿·梅奥。梅奥曾经提出一个论断,人们渴望彼此之间保持工作关系。赫胥黎大声说,算了吧,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只能经历刀俎之苦,截长补短了。赫胥黎的讽刺是站在了更高层面的政治伦理,梅奥则是实证主义态度。两者冲突,也在情理之中。
赫胥黎在无奈之下,提出唯有人人保持自由的心,才是冲破“美丽新世界”的力量。这话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心灵鸡汤了,好在德鲁克及时给他补了锅。
单从文本角度来看,德鲁克和赫胥黎是保持相同的批判立场的。赫胥黎认为,强调整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的社会新伦理正在取代强调个体价值至上的社会旧伦理。在这套新伦理体系中,个体要通过自我调节,不断适应更高的集体要求。“基督教宣称安息日特为个人而制定,实乃大错特错,与之相反,个人是为安息日而存在。”原子化的个人聚集到一起,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像白蚁集群那样成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社会不过是一个个组织,个体没有生命感、没有存在价值的组织而已。在这样的组织里,存在的只有工具价值。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赫胥黎斩钉截铁地说,“人类不管多么努力,也无法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他们只能创建一个个组织。如果他们试图创建一个社会有机体,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仅仅是创建一个独裁体制。”
此时,该轮到德鲁克登场了。
与赫胥黎观点略有不同的是,德鲁克并不认为存在着新的社会伦理。相反,同样是对极权社会的观察和警惕,德鲁克提出新秩序和新信条的缺失正是法西斯上台的主要原因。“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欧洲宗教和社会秩序崩溃的结果。造成这些秩序崩溃的最终也最具决定性因素的是: 欧洲群众对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彻底崩溃。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建立新秩序”。
随着欧洲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公司相继涌现。一开始,人们认为生产单位的扩大可以带来无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进而带来相应权力的扩大。事实却是,大公司特有的层级制度造就了一大批“中间的特权层”。而这种层级制度似乎带来了社会的空前稳定。人们幻想的新秩序并没有到来。
亨利·福特带给了欧洲极大的表率作用。一方面人们渴望随着机器化生产获得更好的生活,一方面又深知基于机器逻辑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带来自由和平等。焦虑的情绪蔓延在欧洲大陆上空。“经济人”的末世正在到来。
从在心灵层面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灵性人”,到从智识层面追求的“智性人”,到在政治层面追求的“政治人”,最后到“经济人”,自由和平等范围越来越窄,逐渐收缩到了经济领域。然而,当时欧洲的政治现实和工业化进程却给了自由和平等一记闷棍。
“没有一个关于人性的新概念蓄势待发准备取代经经济人,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加之基督教在政治舞台上的不断衰落,人们找不到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在机器中与周遭隔离,他们和社会失去了理性的关系。同时,他们又无法接受机器的意志和目的,遂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流浪者”。
没有了“自由和平等”作为目标,理性秩序的基础就不存在。极权的野蛮生长正当时。
过度组织化
本是流浪汉的希特勒深知如何聚集并发动“流浪汉”。既然新秩序没有到来,旧秩序又不存在了,那就捏造一个外表酷似新秩序的超级组织吧。人们不是没有归属感吗?人们不是没有统一的目标吗?那就用“组织”来收留他们,用统一的行政指令约束他们,用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洗脑术驯化他们。
在“时代周刊生活编辑部”编写的《第三帝国》丛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要叫一位诺特海姆(德国的一个市镇)的公民来确定纳粹党代表什么,这并不容易。大体上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重振雄风、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民族自豪感的人民德国。但是,要看出纳粹党反对什么,并不困难。”不知道建立的是什么,但是知道反对的是什么(即反对一切),这恰恰是德鲁克总结的极权社会的一大特征。
因为他们没有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性的秩序信仰,所以要通过组织把人们收编,告诉他们要反对一切组织所反对的,拥护一切组织所拥护的。组织随即成为极权操纵民众的有效手段。
德鲁克说,“一个以组织而非秩序和信条作为基础的制度,如果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产生严重的后果,就表示它在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上也有致命的弱点。”道理不难理解。组织不是人的目的,人才是人的目的。如果一个人加入组织后,发现自己不过是组织的手段或者工具,价值观将荡然无存。在任何社会制度中,组织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成为自己的路径和发现自己的结果。
纳粹打造了一个空心化的组织,他们不得不通过以宣扬新秩序为名,以不断制造新组织为实,来实现控制。因此,极权政府需要越来越多的组织。据说纳粹每六个月就有一次新秩序宣言,盛况空前,人民群众热情高涨,他们总以为又要有新的组织来满足自己了。当然了,组织仅仅是组织,它和民众无关。
极权组织的另一个特征是万能的“领袖”。这位领袖超越了人类,它就像是神的化身,他脑子里的欲望就是民众的秩序,他一手制造的帝国往往在接近完美时崩溃。
但就是这样一位神,也逃脱不了自我制裁的后果。当盟军挺进柏林的时候,隆隆的炮声把希特勒从地下掩体的床上震了下来。得知实情后,他打电话给前线的指挥官,谁知道将领们并不承认。希特勒怒骂,“你们这群官僚”。希特勒骨子里是个流浪汉,他厌恶官僚,却又不得不搭建一个精密复杂的组织,豢养一大批官僚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神话。
领袖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此。这就像民众一样,他们在相信着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矛盾从头到尾都存在。
“知识人”的未来
“在缺乏真正的秩序的情况下,民众用组织来替代秩序;在没有神可以崇拜、没有关于人的概念值得遵循的情况下,他们只好膜拜恶魔,这些强烈显示了:民众亟需一个秩序、一个信仰以及一个理性的人的概念。”德鲁克这句话中,“人的概念”出现了两次。如果我们不想去考察那些繁琐的关于“人”的种种解释,只需用康德那句短语——“人是目的”——就足够了。
“经济人”的概念注定会死去。虽然青年德鲁克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洞见了一切,但是他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新名词。取代“经济人”的那个人,一定是新秩序的表征。因为每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基于一种涵盖了人的本质、社会功能和地位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技术的集合,是社会辨识自身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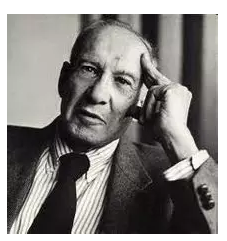
彼得·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
德鲁克在40年代把“管理学”开宗立派,60年代末提出知识社会,两者相加便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人只有在知识社会中,才有可能成为自身的目的。知识而非经济基础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时,经济的平等和自由才会真的到来。
在经历了断裂的年代后,知识时代的人应该被称为“知识人”。他们不会被组织困住,因为“知识人”心中有明确的信条,这个信条不必须由单一的组织承载或者兑现,那就是专业技能。
作为专业的管理在此时出现,无疑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色彩。它是属于知识社会的,是超越组织的。它的目的不是变着花样打造一个又一个没有生机的机器,而是把人之所有归还给人,而组织则从目的也变回到了手段。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管理的任务是打破组织的乌托邦,为“知识人”在社会秩序中遨游提供一切指导和帮助。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