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值中国网自2008年开始和徐景安先生共同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座谈会”,迄今已进行了多次。开了数次会,感到无论什么话题,要在知识分子中达成共识都殊为不易,但起码,应该努力就当下中国的种种问题,营造一种平等对话的氛围。喝了多年“狼奶”,很多人已经不知尊重异议为何物,越是后来者,态度反而越趋极端。
在第三次会议上,盛洪先生主讲《个人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我有感于与会者对个人主义的基本概念所言不清,强调指出不同派别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不同地域的个人主义也是不同的,德国、英国、法国的个人主义全部不同。如果不对个人主义做细致的辨微功夫,我们的讨论非但没有创造的价值,反而会有破坏的作用。
例如,与会者中,仲大军说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张祥平则称《论语》里就有个人主义。推而言之,有一位叫乾泉的先生说《易经》里就有民主,张祥平甚至说,西方有的东西,只要你能够说出来的,我们中国都有。概念的混乱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短处——模糊性大,界限性弱,缺乏精确分析和逻辑论证,重玄轻用,粗疏鄙陋。如果一个人从学理的逻辑上导出自己的东西,而其他人却用玄学思维发起驳难,这岂不是鸡同鸭讲吗!
没想到我的这番批评大大得罪了乾泉先生,他恶狠狠地说:“反《易经》就是反革命!”这种态度与论坛第一次会议上,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语重心长所谈的 “三宽”境界——宽容、宽厚和宽松,相差何止天地之远。朱先生不幸于2010年5月9日仙逝,今天,纪念他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重温他的“三宽”讲话,反省我们何以把“宽”的路越走越窄。

朱先生说:
“我原来在地方工作,20年前才来到北京,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反复多年的争吵,……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睁眼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过?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赖?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1986年,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我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当时我说:
“今年(1986)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就是“三宽思想”的缘起,朱本人也因此被誉为“三宽部长”。这一思想,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显得那么卓尔不群、振聋发聩。宽容、宽厚、宽松,可以说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诉求。这些年在中国建设公共领域的呼声渐起,而欲实现这样的目的,必须朝两个方向努力:一是争取公民权利以及公民社会活动的独立自主,二是反对商品生产和消费对公共生活的侵蚀。从历史上看,公共领域本身就是在反抗一体化政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性”、“公共美德”与“公众舆论”支持了言论、出版、结社及其他公众共享的自由。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争取自由权利,另一方面,我们也需培育良好的政治文化,鼓励公共事务的参与、公共的责任、美善言行的演示、正派的习俗道德、同情和宽容以及对弱者的保护等等。哈贝马斯说得好:“一个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需要的东西比宪政国家的制度保障还要更多;它还需要文化传统和社会化范型的支持精神,需要政治文化,需要一个习惯于自由的人口。”

中国为建设这样的公共领域做好准备了吗?从臣民到公民的路既漫长又艰难。找到足够多的理性而自我导向的个人,把各自的利益融入更大的共同善,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990年黎安友和史天健在中国开展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政治行为和态度的调查。调查采用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提出的政治-文化变量,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政府影响、体制作用的感知以及对持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的容忍度都相对较低。尽管国家相对来说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更全面的控制,大多数中国公民不能识别这种控制。只有5.4%的回答者感受到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18.4%的人感受到一定影响,71.6%的人不认为有任何影响。就全国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来看,回答有轻微的变化,分别是9.7%,11.7%和71.8%。数据也显示,在中国,教育程度不同的每一类回答者,都比《公民文化》中所调查的五个国家的相似者,显示出了更低的对政府影响、体制作用的感知。另一方面,在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国人当中,存在 “相当大的对政府的信心”。57%的回答者表达了受到政府平等对待的期望,只有24.2%的人未作如此回答。
在政治容忍度方面,只有17.4%的人愿意允许持不同意见的人表达他们的观点,只有10.3%的人愿意允许那些不受欢迎的观点得到传授和出版。同样,教育程度不同的每一类回答者,都比《公民文化》中的五个国家的相似者,显示了更大的不容忍。调查结果显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可能困难”。“相对较低的对政府影响和体制作用的认知以及较不容忍的态度,都可能成为民主化的障碍。人们可能不愿参与政治,可能赞成对他们不同意的主张进行压制。”
除了政治,当代中国在道德上强求一致的情形也很普遍。社会常常在道德问题上作出判断,并习惯于运用法律,强制性地把社会的道德贯彻下去。我们都还记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恐惧“多数的暴虐”,更恐惧“社会本身是暴君”,甚至认为后者的危害比前者还大。而他对社会暴政的戒心,并不是由于社会上的多数人打算将行为乖张者绳之以法,而是由于多数舆论可能对少数特立独行的人形成看不见的压力,逼使不同的意见和个体的创造性就社会之范。如果个体性、首创性真的要有所发展,那么自由原则所要求于社会的,将不只是法律上的豁免,还必须有道德上的宽容。
这种宽容在互联网上也格外重要。在大量的私人行为经由网络变得高度可见之后,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能够容忍这一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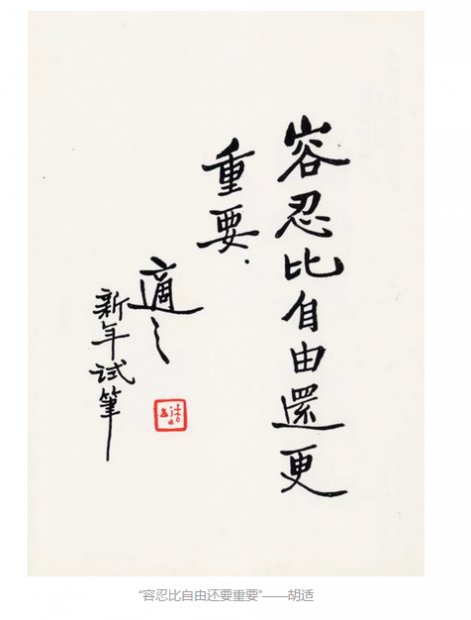
一贯强调容忍的重要意义的胡适,曾讲述过一个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概念:“正义的火气”。他说:“‘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五四学人不独胡适有这样的思考,钱玄同也曾在致周作人信中反思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换言之,胡适和钱玄同都察觉到了五四时期“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语)的态度其实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当今时代,“正义的火气”越来越旺,而宽容的精神却越来越少。朱先生说得好:“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越过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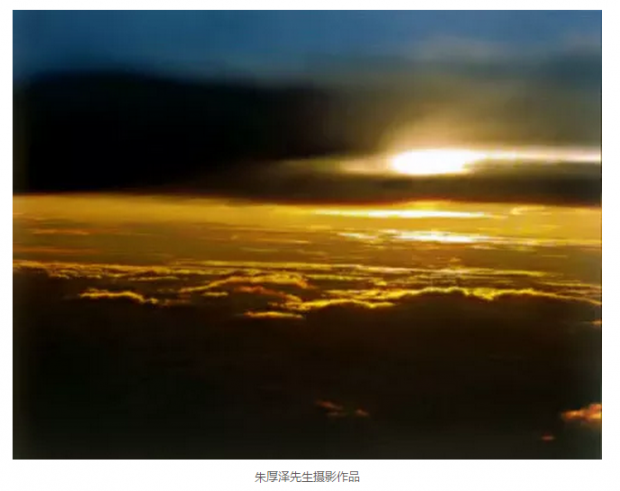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