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在医院,在公交车门前,在地铁入闸口,你有见过拿着手机,在二维码和摄像头前“进退失据”的人吗?
在我们生活的各种公共空间里,我们随处可以见到这些“数字弃民”。学者胡泳把数字化进程比作一辆列车,他认为,很多人会在“搭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一个误解:人人都会上车,只是时间早晚。
胡泳认为,这样会忽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许多人根本就上不了车,而是被彻底地甩在这辆列车之外。由此,数字化社会便产生一个有害的副产品——“数字弃民”。
作为中国互联网、新媒体及数字化变革领域的主要启蒙者和思想提供者之一,胡泳对于“数字弃民”背后的“数字排斥”现象有日常体会和深切思考。近日,我们和他聊了聊数字弃民、数字排斥这些在防疫大背景下凸现出的群体、现象,并请他谈了谈今天对于“传统行业数字化”和“科技向善”这些话题的新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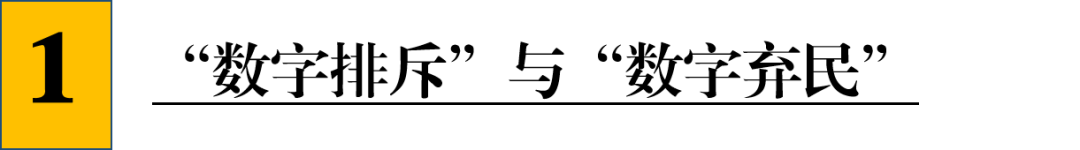 边码故事:看到你写过父母去银行办业务时,遭遇的数字化困扰,能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吗?
边码故事:看到你写过父母去银行办业务时,遭遇的数字化困扰,能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吗?
胡泳:我其实一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银行需要大规模地做人脸识别。
你可以说人脸识别能有效地进行身份认证,也能防止诈骗,但很奇怪的是,在人脸识别技术出现之前,银行难道就不做业务了吗?
我父母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我90多岁的父亲,做人脸识别的时候,经常过不了关,摇摇头、眨眨眼、张张嘴这些对平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对他来说并不轻松。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高度耳聋的老人,他的耳朵几乎听不见,所以这些动作他每回都要重复若干次,但有时系统就是不认为他已经眨眼了。
我母亲患有严重的腰疾,出门必须坐轮椅,她是没有办法自己下地行走的,但某些业务,银行要求本人必须去现场办理,也必须做人脸识别。机器采集图像时,距离地面有一定高度,所以最后只能由我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一人架一边,把老太太从轮椅上架起来,半搀半抱地对准摄像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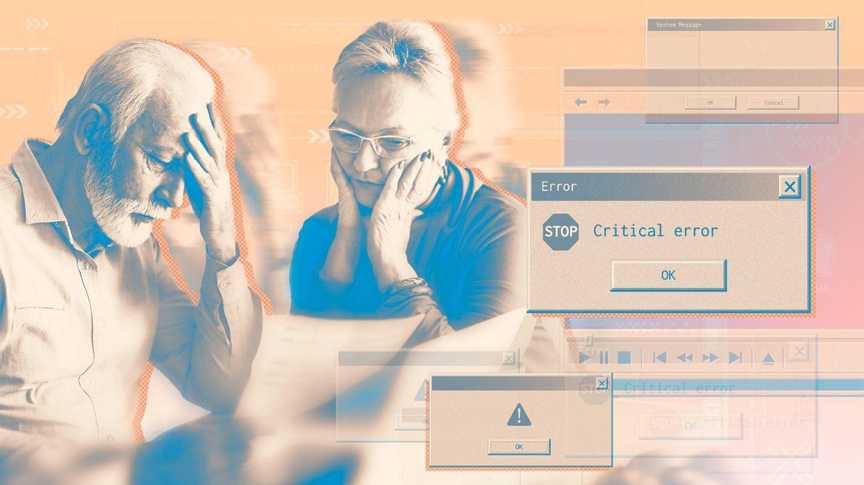
边码故事:对此,你有哪些体会和反思?
胡泳:我觉得第一,银行是不是非得要通过人脸识别,让客户办理业务?第二,对老年人这个群体来说,是不是有人脸识别以外的其他替代方案?
如果一个失智的老人,一个失明的老人,一个失聪的老人要去银行办业务,你怎么应对?都必须去做人脸识别吗?这是很荒唐的事。
边码故事:这些被人脸识别这类技术边缘化的群体,会不会越来越被数字技术排斥?
胡泳: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如今你去任何一家医院,门诊大厅里都有各种各样的自助设备,挂号、缴费、拿报告单……你都需要在自助机上操作。
但其实有相当多的人根本不会使用自助机,那么医院的工作人员就会觉得,自助机这么简单,你怎么就不会呢?这其实是在要求人必须和机器打交道,必须和某个系统打交道,如果你不会,那你就是愚笨,就等于没有文化,甚至还会被嘲笑和训斥。
数字化的一个常见概念叫“缺省”,缺省就是默认,即系统的默认状态。在缺省设置上,有关服务的数字化应采取包容性方法,而不是强制性方法。如果公民不能在线履行义务或觉得过分困难,则不应强迫他们在线履行。
假使众多服务都被缺省设置为“数字化”,那么非网络用户就会因此面临边缘化的风险,从而对一定人群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产生影响,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数字排斥”。 在当下的现实中,需要对很多服务的运行方式进行一定的更改,来纠正数字排斥的影响。例如,健康服务不应一切都转入网上进行,必须保持必要的面对面服务和在线处理的替代方法。
用更形象化的比喻来讲,如果我们把数字化进程比作一辆列车,很多人会产生一个误解:人人都会上车,只是时间早晚。其实这样想会忽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人根本就上不了车,而是被彻底地甩在这辆列车之外。由此,数字化社会便产生一个有害的副产品——“数字弃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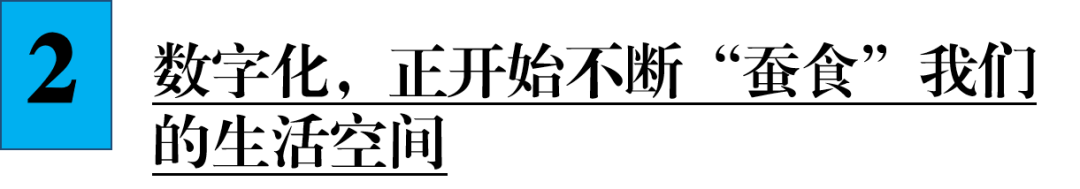 边码故事:这些被数字排斥的数字弃民,自身会不会因为无法完成数字化操作而愧疚?
边码故事:这些被数字排斥的数字弃民,自身会不会因为无法完成数字化操作而愧疚?
胡泳:很多人会感到不好意思,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技术的问题。我父母如果没有我帮助他们克服各种技术障碍的话,他们办理银行业务和社保、打车和就医等时,恐怕寸步难行。
其实这些事情的核心,源自数字化的不断扩展:生活中很多与数字化没什么关系的事情,由于数字化“殖民”的“地盘”和“疆域”越来越大,开始不断“蚕食”我们的生活空间,这也导致了很多本来和数字化不发生交集的场域,都渐渐地被强行变成数字化的空间。
边码故事:在新冠疫情的防疫过程中,有没有数字化“蚕食”生活空间的例子?
胡泳: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而开发的一款数字工具,其用途被扩张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层面,比如健康码,它本身建立在大数据里第一重要的地理数据基础之上,地理数据对个人而言,是构成个人基本行动自由、行动空间的重要数据,也建构了大数据和个人隐私的一种强关系。
这时,因为疫情而引起的公共利益和对个人隐私的尊重之间是需要平衡的。甚至可以这么讲,个人隐私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公共利益。
但现实中被公开的感染者的流调,让疫情新闻变成了讲述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努力工作的底层辛酸物语,或者一个中产去高档商场购物、去游乐园游玩等的生活方式评判,围绕新冠患者的流调、行踪,产生了网民的围观和狂欢,大家热衷于传递这些东西。这说明我们在保护他人隐私方面的意识非常差,但关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早已写入《民法典》,也写入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我们国家对隐私保护的体系其实非常完备,甚至可以媲美欧盟。但一到了现实里,大家就会觉得个人隐私要为现实需要让道。
很多数字工具被开发出来后,只有具备高度的克制、自律,才会使得记录普通人的数据不会被滥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它具有方向性。不难明白,技术中立论给了发明家和工程师等很大的帮助,似乎免除了他们对自身发明物所引发的不良影响的责任。

边码故事:像这类因为数字化被滥用造成影响和损失的人,可以叫做数字弃民吗?
胡泳:这个要看对他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数字弃民是怎样被数字化排斥的?我们可以把数字排斥可分为四大类: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地理位置排斥。
自我排斥者指由于技术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感到自己落伍而因此停止参与数字世界的人。财务排斥所显示的数字鸿沟与付费能力有关:低收入人群无法为连接的前端成本、具有上网功能的设备和上网本身的持续成本支付费用。
技能排斥是指,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互联网过于复杂,他们不仅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而且缺乏对互联网工作原理的理解。比如很多老年人本身并不拥有健康的躯体,这也对他们参与数字化进程时构成了巨大障碍。
地理位置也会产生排斥。在偏远地区,宽带和移动基础设施较差(或根本没有),这意味着有些农村地区的人们面临着物理服务以及在线服务的双重受限。
 边码故事: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数字排斥现象变得比较明显,同时,未来会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患上“数字化依赖症”?
边码故事: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数字排斥现象变得比较明显,同时,未来会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体患上“数字化依赖症”?
胡泳:某种程度上看,数字弃民无法成为社会正常运转过程中合格的一员,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交集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这是悲哀的或者说令人遗憾的现状。
另一方面,那些高度依赖数字化的人,他们也不见得就不会堕入到一种比较悲哀的、令人遗憾的数字陷阱中去。有时候我们可能习惯于日常生活里的数字化了,以至于忘记了数字化背后其实是有很大代价的。
我有一个学生,去年研究过河南特大暴雨这个事件。河南暴雨其实是现代生活当中一个极为罕见的突发事件,或许也只有在这种罕见的案例中,你才会发现,我们为所谓的“先进生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河南暴雨不仅造成停电、停水、停煤气,也一定导致停网、停电话,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一夜之间,回到一种前现代的生活状态。
这时我们发现,那些邻里关系活跃、日常交际频繁的小区,反而能够团结起来并组织自救,而那些依赖数字化的流动青年,与社会网络脱域后身处悬浮状态,他们是高度数字化的一族,是原子化的个人。这个群体平常下班回到房间里,就完全依赖数字技术工作、购物、聊天、娱乐。这群原本最高科技装备的群体,在暴雨的极端冲击下其实是最狼狈的,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传统社区互助的可能性,从而集体沦为“数字难民”。这其实是一个警钟,向所有人抛出了一个问题:数字化究竟是不是一切?
数字化本身并不是永远安全、永远在线的一个基础设施,这从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就可以观察出来,当微信、支付宝因为断网而无法扫码,ATM机因为断电、断网也无法取款,这时家中是否有现金都成为你能不能吃上饭的关键。所以当你患上数字化依赖症后,一旦出现极端情况,顷刻之间你就会沦为“数字难民”中的一员。

边码故事:数字化发展到现在,当下你对它的看法是怎样的?
胡泳:我自己多年以来一直是推动数字化的,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不用过多举例,我们经由数字化,达成了以前很多达不到的目的,完成了很多以前无法完成的事业,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但数字化在深入了社会这么多年以后,我们要意识到一点:我们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数字生活与现实生活并行不悖的局面,我们不大可能回到没有数字化的时代去,同时也不大可能完全进入数字化空间,而把现实生活抛诸脑后,这就是类似河南暴雨这种突发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反思。
既然数字生活和现实生活对我们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及某种平衡关系。
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关于数字化的负面内容,是因为我有一种忧虑。前些年,我们把现实中的东西不断向数字化空间迁移,活动也好,关系也好,身份也好,全都迁移到了虚拟空间中。
现在呢,我们正在看到一个局面,那就是数字化空间正在侵吞现实空间,我觉得这是真正值得忧虑的事情。也就是说,数字化的“地盘”在不断扩张,扩张的过程中,它以一种“技术给你带来好处”的方式,掩盖了技术让我们付出的那些不可承受的代价。
边码故事:你现在对“科技向善”的理解,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胡泳:其实当年腾讯提出科技向善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是腾讯的三重冒险:第一,它可能带来“意义困境”,给腾讯的官方解释造成巨大压力;第二,它在抽象概念与具体操作之间难以做到无缝连接;第三,在口号之下可能发生的所有技术滥用乃至恶意使用,都会被公众以放大的目光来审视、以强烈的舆论来审判。
如果你从一个笼统的角度来讨论科技向善,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务虚的、比较高标准的说法,但对企业来说,把“科技向善”的内涵加以缩小,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某个具体的产品或服务是不是向善?
如果我的产品本质是向善的,我的服务是向善的,我的创新是向善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家企业的科技是向善的。但如果我生产出来的产品,某种程度上严重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或者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一些例子,不仅不以人为本,甚至是科技助恶,那么“科技向善”就走到了它的反面。
从一个更高的指向上看,一家企业不一定要天天高唱企业社会责任,因为企业毕竟是企业,企业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但是,最起码企业可以问一下自己: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是不是能带领大家,去创造一个拥有更大社会意义的事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你需要这些东西去对外宣传,或者去获得它所谓的公关价值,而是说,如果你找到这样一份事业,它最终会让公司受益匪浅,因为你不仅可以让员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才总是会为那些有意思的事情所吸引、汇聚,同时也可以为员工提供前进路上更大的动力。
比如,你作为某一个组织或某一个机构的一员,你可以跟世界分享什么?你又能怎样帮助到他人?其实这些事情也并不需要那么高调,是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需要时时刻认真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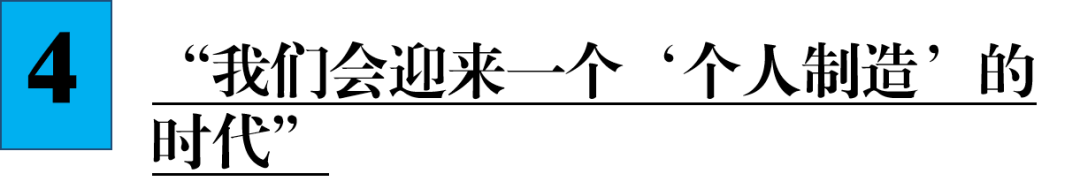 边码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也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对这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互联网扮演的角色,你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边码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也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对这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互联网扮演的角色,你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胡泳:通常我们讨论数字经济时,我们会把它分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或者说关注度比较高的是数字产业化,因为它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影响。
我们姑且把ICT企业称之为数字化的原生企业,数字技术在不断进入传统行业的过程中,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很多威胁,然而经济当中最大头的一部分,其实是产业数字化。
相当多的传统企业,必须围绕数字化展开转型,这一部分大概会占到整个数字经济中的4/5。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数字化本身像一个黑洞,对不同产业,它的辐射距离都不一样。有些产业距离黑洞近,所以很快就会被黑洞吸进去,因而产生巨变,比如媒体、广告行业;有些辐射距离稍远,比如零售业、教育业、餐饮业、旅游业、交通出行等,这些属于被辐射的第二圈。
再远一点或者说再外围的圈,可能是金融业、地产业、批发业等。最后我们会发现,距离数字黑洞辐射最远的行业中,就有传统的制造业。
边码故事:你怎么看传统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困境?
胡泳:从理想的状态来看,传统制造业会迎来订制化生产和3D打印的局面,这些会彻底地改写整个的大规模制造,我们应该会迎来一个“个人制造”的时代,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社群制造”时代,因为个人和社群在未来这种理想状态下,是完全可以在家里或者社区,设计、生产出属于你自己的产品。
我们一定会生产出更牢固、更轻薄、更节能、更耐用的产品,在生产线上出现的一定会是机器人,因为它比人工更便宜,虽然现在很多机器人还不够智能或者成本过高,无法立刻投入大规模应用,但我觉得假以时日,随着新一代智能技术的更新、市场的快速适应,一定会大大降低产品设计和制造的门槛。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最终可以想象的是:所有的制造业的工厂一定都是自动工厂,未来不太可能有非自动工厂了,那么这里面就一定会释放出大量目前在制造业中工作的工人,个人认为这可能是未来社会潜藏的一个巨大问题,也就是制造业工人的出路问题:他们到底能去哪里?
按照以往的经济发展经验,大家可能会比较乐观地说,尽管技术被应用在传统行业后,会有很多人因此而失业,但总会有大量新的岗位被创造出来,这些工人会被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吸纳,因此不会造成特别大的社会波荡。
但我觉得目前一切都很难说,未来政府需要以此设计,或者是说施行一整套不同于工业社会的那种保障体系。工业社会其实是为了避免工人出现类似问题,于是开发出福利国家的种种措施,比如失业金、最低工资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对应工业社会的产业结构的。未来如果一种新型社会到来,我们可能会面临这种工作机会的巨变,或者是很多就业机会的丧失,那么政府将不得不开发出一整套新的应对手段。
举个例子,政府可不可以拿出因为技术改造而带来的红利里的一部分,按照人头来发放?就直接就发给每一位具体的个体,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