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编者按:
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教授胡泳照护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的经历被媒体报道,在社交网络成为热点。高龄失能老人照护,并不是胡泳教授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高龄失能老人需要照护,这也成为整个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家庭照护是中国老人照护的主要方式。家庭照护也存在很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南方周末特邀胡泳教授撰写系列文章,以亲身经历和学理思考,探讨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护,为什么这么难。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家庭照护者是家庭和整个社区的榜样,为更人道的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因此,“谁来照顾照护者”的问题,是发展一个照护型社会必须投入很多力量去解决的。
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照护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无论做多少努力,家庭照护者还是会准备不足。这既是缘于照护者的多重和不断演变的任务和角色,也来自照护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质,以及照护者责任的日益众多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家庭照护比过去更加密集、复杂和持久,照护者很少得到充分的培训来承担他们的工作。这对照护者的健康和福祉产生很大的影响。

大量证据表明,许多护理人员都经历了负面的心理影响。其中一些照护者的风险高于其他护理人员,尤其是那些长时间照顾患有晚期认知症的老年人的照护者。当然,照护者也能从中获益(详见后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正面影响可能与照护的负面影响共存。
我作为“高需求老人”的照护者,四年的照护体验可谓五味杂陈,时常感受到锥心的痛苦,但令我在痛苦中坚持下来的东西,显然也包括我自认为从照护经历中获得的教益。长期跟踪的研究发现,照护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既可能产生有害后果,也可能产生有益后果。照护者可能会同时经历情绪困扰和心理满足与成长,这些影响并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
照护的负面心理影响
照护的影响各不相同,取决于个人内在和外在的特征。不过,关于消极影响的证据远远多于积极影响的证据。为什么家庭照护对照护者的不利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太多关切需要照护的老年人的困难,却倾向于忽视照护者照顾他人时产生的身体、情感和精神疲惫状态。这背后导向的问题,被我归结为“谁来照顾照护者?”
照护的消极心理影响涵盖一系列方面,从认为照护有压力,成为负担,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由健康专业人员诊断出临床抑郁症,到生活质量受损,会走过一个从小到大、从轻微到严重的进程。

大量可靠的文献记录了与非照护人员对照组相比,照护人员的心理困扰率更高。20多年里,证据一直在稳步积累,包括大量单独的临床研究、多项系统评价以及越来越多的基于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这些文献大部分基于横断面研究,其中将照护人员与可比的非照护人员进行比较。在文献中,家庭照护通常被描述为一种负担沉重的角色,具有慢性压力体验的所有特征。基本上存在一种强烈的共识,即照顾患有慢性病、残疾或者认知症的老人是一种负担和压力,尽管家庭照护者为社会及亲属提供了重要的服务,但他们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压力可以被定义为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耗费或超出了某人的资源,并危及他/她的福祉。如果照护者没有足够的内部(信息、技能、应对行为)和外部(经济、其他家庭成员的帮助、正式照护)资源来适应照护环境,他们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长期在被照护者病情逐渐恶化的情况下提供护理,几乎或完全没有缓解的希望,例如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毫无疑问属于压力源,而且是慢性压力源。

纵向研究可以更令人信服地证明照护与心理困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些研究跟踪了个人进入照护角色、整个照护过程当中以及离开照护角色的过程。这些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进入照护角色时,幸福感会显著下降,随着照护需求的增加,幸福感会进一步恶化,而照护对象死亡后,幸福感会恢复。干预研究表明,当照护者自身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其健康和幸福感会得到改善,这也支持了照护与幸福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照护者普遍存在负面心理影响,例如报告存在严重的情绪困扰,照顾最严重残疾老年人的照护者,报告有焦虑和抑郁症状。认知症照护人群的抑郁症发病率甚至更高。他们的总体主观幸福感较低。很奇怪的是,当照护对象搬到像养老院这样的长期照护机构时,照护者的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会持续存在,严重程度与其提供家庭照护时相似。事实上,家庭照护者提供的亲身照护越多,他们的此种痛苦就越高,对养老院工作人员提供的照护的满意度就越低。

对照护者心理健康影响的长期纵向研究表明,负面影响在护理过程中各不相同。尽管在某些关键时期,照护者最有可能出现心理困扰。比如,在护理开始和护理结束的过渡时期,负面影响最为明显。特别是,照护者刚过渡进入照护角色之时,是抑郁症状增加风险较高的时期。当然,照护时间越长,照护者的抑郁症状增幅就越大,生活质量也越差。事实证明,长期照护造成的身心伤害也是长期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照护者的免疫系统甚至在其照护角色结束三年后仍处于紊乱状态。而长期住院患者的护理者抑郁症状严重,可持续一年以上。
照护的正面价值
尽管相当多的照护者会经历负面的心理影响,但不少人也发现照护很有价值。就我自己而言,照顾父母四年过去了,我感受到自己在各个层面所经历的深度疲惫,但我也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它。陪伴所爱的人踏上最后的旅程是一种恩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拥有。如果父母从我的陪伴中获得安全和安慰,我最大的收获是心灵的宁静。
照护的正面心理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比如,照护者对生命会更加珍惜。当你对所爱之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可能会改变你对生活的看法和你自己的人性。被照顾的人会真诚地感激你,知道你已经给出了最宝贵的礼物——时间。感激之情可最大程度地减轻压力。

照护者在得到护理对象的认可和感激之后,还会收获其他益处,比如自尊心增强。通过积极评价和精神追求找到意义的能力是一种有效的应对压力的机制,促使照护者对自己的角色感到自豪和有目标感。照护者历经各种磨练,感觉自己很有能力应对困难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效能的增强,导向的是个人成长。许多调查表明,对于某些照护者来说,照护可以注入信心,提供处理困难情况的经验教训,让他们感觉更接近照护对象,并让他们确信后者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尽管照护经历会给家庭带来压力,但它十分有助于加强照护者与照护对象的关系。特别是在奉行家庭主义价值观的东方文化中,照护提升了对家庭成员的强烈依恋、奉献和认同感。孝道的价值是亚洲社会中独特的概念,在照护框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照护者更有可能体验到孝道和对职责的义务,这些观念与社会文化规范交织在一起。
说到这些,我们并不是要贬低照护者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承认,照护并非一种完全消极的经历。从照护中感知到的益处是照护者的重要心理资源。当照护经历具有令人满意和有益的积极方面,它就可以作为负面后果的缓冲来改善照护者的心理健康。
关爱家庭照护者群体
综上,大量文献,包括基于人群的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相当一部分照护人群经历了负面的心理影响,尽管照护本身也不乏一些积极的影响。
无论使用哪种心理健康指标,照护者的痛苦程度都足以构成公共卫生问题。就像我们需要制定干预措施和公共政策来满足被照护的老年人的需求,我们也需要采取类似的步骤来关爱照护者群体。
在美国,超过30个州通过了《照护者建议、记录和赋能法案》(CARE Act),要求医院确定家庭照护者,在患者出院时通知他们,并提供他们将被要求执行的任务的基本教育。其他政策变化可以是通过增加带薪休假的数量和鼓励雇主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加强对照护者的财政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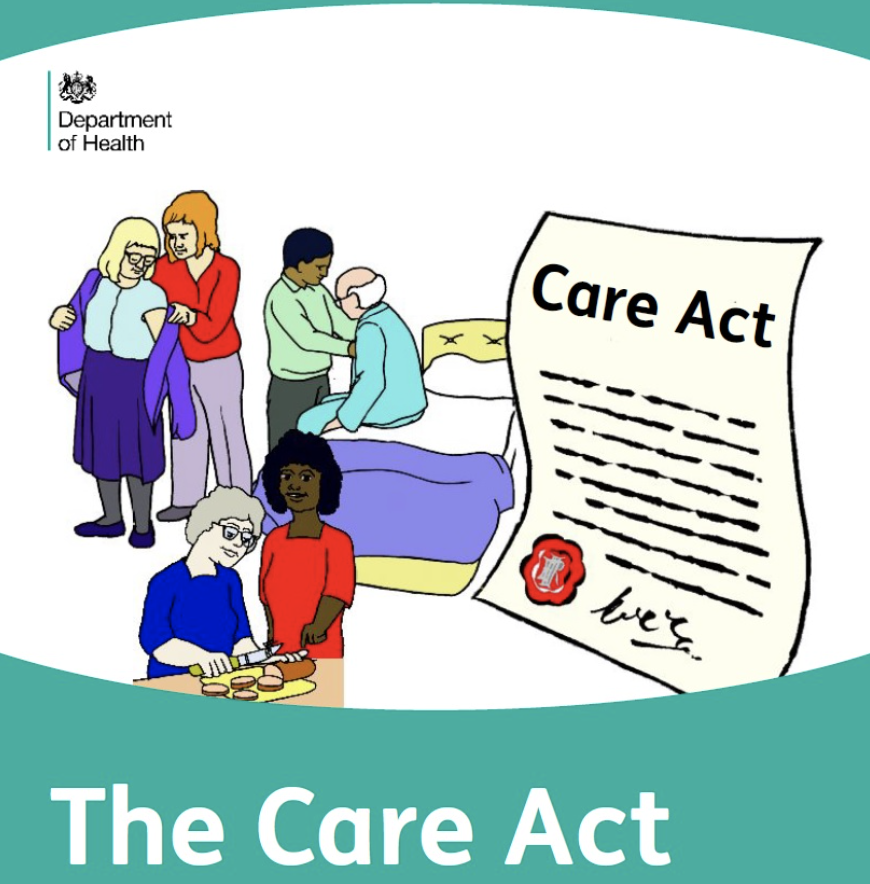
而要想赋能家庭照护者克服他们可能遇到的挑战,医务人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改善双方互动、支持和教育的方式。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把照护纳入视野之中,评估和认识照护人员的负担。一旦发现照护者出现问题,早期干预可以帮助他们履行职责,并确定所需的支持,以在提供照护和保持身心健康之间取得平衡。此外,心理教育干预和应对策略可以帮助缓解照护人员的痛苦。干预措施需要针对特定的照护人员亚群体进行量身定制。
很多家庭照护者密切参与为老年人提供照护的活动,但并不因此获得任何经济回报,他们是长期照护慢性病、认知症、残疾、年老体弱者和临终者的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单靠现有的医疗和社会服务系统根本无法应付实际需要照护的人群。所以,除了政府、企业和医院,我们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支持团体为那些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癌症和其他严重疾病患者的人提供帮助,让他们获得起码的喘息时间。

家庭照护者是家庭和整个社区的榜样,为更人道的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因此,“谁来照顾照护者”的问题,是发展一个照护型社会必须投入很多力量去解决的。由于这个群体的不可见,社会对此种“劳动力”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它显然不可持续。虽然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和医疗护理更加复杂,对护理人员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由于结婚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和地域分离加剧,护理人员的供应却在不断减少。在美国,2015年,每一位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7位潜在的家庭护理人员。到20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降至4:1;到2050 年,每个老年人的潜在照顾者将少于3人。
对许多人来说,照顾亲人提供了巨大的意义和满足感。它可以提供时间和空间来建立联系,否则这种联系就可能不存在。因此,目标不应该是减少家庭照护,而是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

对我来说,当我母亲在治疗了一段时间社区获得性肺炎出院之后,医生提醒我,你的家庭照护负担将大大增加。听着他们这样交代,我的脑中一片茫然。我想我的情况绝非特例。医院有将家庭照护者纳入有关患者治疗计划的重要决策中吗?尽管医生期望他们在家中执行这样的计划。我茫然失措的原因是,医生告诉我,必须学习执行复杂的医疗任务——注射、更换导管、开始鼻饲、吸痰、吸氧和雾化——但谁来负责培训我呢?
所以,我不得不自我摸索如何帮老人在床上翻身而不冒背部拉伤的风险,如何想办法加强老人的运动而不让她得静脉血栓,如何在老人便秘的时候给她灌肠,如何掌握注射胰岛素的正确方法——怎样捏皮肤,以什么角度插入针头——以及如果血糖、血压、血氧等等水平过低,要注意哪些迹象。
在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来帮我一下啊。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