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沙沥金
人类无疑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是否有道德上的毅力来拯救我们自己,使我们免于真正的灭亡。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利用过去来更好地理解当下。
本专栏意在对选定的个人的生活和贡献进行一种富于当代意识的文化调查,虽然历史可能是不稳定的,但它确实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晶。一群特定的男人和女人,塑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时也在他们身后的文明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找到相信这个世界的理由,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以展望未来时,让我们追随并超越那些拒绝接受历史压迫的抵抗者,那些让我们热泪盈眶的作家,那些震撼我们灵魂的艺术家,那些敢于书写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的诗人,那些以持续的智力投入来守望社会的思想者,以及所有从未被眼前的限制所打败的异类。
——胡泳
01
“试着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
在生前最后一部文集《重点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2011)中,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谈到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时,修改了中国古老的咒语“生不逢时”,指出对于作家而言,更令人扼腕的是“生不择地”。接着她引用了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一句辣评:“来自陌生的地区是一种特权,在那儿人们很难逃避历史”——想想这两位写作者的出身,波兰无疑便是这样的写照。
至少200年来,诗歌在波兰文学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当一个国家基本的生存权不断受到威胁,在历史上那些最戏剧性的时刻,波兰人在诗歌中寻求救赎和慰藉。诗人在波兰受到特别的对待,但也被要求“认真”写作。甚至可以说,即使波兰诗人觉得要开玩笑,读者也希望他们能对一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比如公民、社会、哲学和存在主义的话题)开玩笑。波兰人尊重他们的散文作家,但爱他们的诗人,并期望从诗人那里获取不平庸的讯息。诗歌在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是波兰所特有的,这既由历史因素塑造,但也是由某些转瞬即逝的却可以清楚观察到的公众偏好造成的。甚至还有一个不完全脱离现实的笑话说,法国和波兰文学最明显的区别是,法国每年出版300部小说和30部诗集,而在波兰,这些数字是相反的。

对于波兰诗人来说,所有这些公众的尊重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负担。他们外向的目光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一种厚重感,这种厚重感似乎是一种被祝福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诺贝尔文学奖眷顾了两位波兰诗人,即切斯瓦夫·米洛什和维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而兹比格涅夫·赫贝特(Zbigniew Herbert)、塔德乌什·鲁热维奇(Tadeusz Różewicz)和扎加耶夫斯基本人也在世界诗歌的前列。波兰出版商耶日·伊尔格(Jerzy Illg)说得中肯:“亚当的诗歌被认真对待令人欣慰,但这种认可是有代价的。定期处理波兰历史上复杂的悲剧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如果伟大的事件在你身边发生,你清晰的感知力就会在喧嚣中消失。”
从波兰的诗歌传统来看,扎加耶夫斯基属于被称为“68一代”或“新浪潮”的文学运动,该群体的目标是“反对意识形态和宣传对现实的歪曲和对语言的占有”。“68一代”是以诗歌参与社会的一代,既源于1968年欧洲的反文化经验,也源于同一时期波兰的政治突破和动荡(1968年学生抗议、反犹冲突,1970年暴力镇压工人罢工)。有意思的是,这一代的特点是他们的诗歌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和八十年代初对政治和社会事务非常强烈和积极的参与,演变为情感疏离、反讽、对世界的观察和形而上学意义的诗歌。
1979年,30多岁的扎加耶夫斯基离开波兰前往德国,并非如常人所想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政权令人窒息的压力,而是为了逃脱反对派令人陶醉的拉力。作为反对派的支持者,扎加耶夫斯基为人们写给当局的抗议信背书并征集其他签名,但他觉得自己在失衡。“人们期望我为运动做出表达,这与做自己之间的平衡是如此微妙。有两年时间,我写的东西很少。作为反对派运动中的一员,我很高兴,但作为一个作家,我很不高兴。”在反对斗争中,他感觉正在失去自己的个人声音。因此,他最终从西柏林的相对距离观察了1980年团结工会运动的诞生和格但斯克船厂工人的罢工。对此他曾自嘲说:“在你的简历中写上‘我去了船厂’是非常好的,而我的简历里没有。”
1982年底,扎加耶夫斯基搬到巴黎,与演员兼翻译玛雅·沃德卡(Maja Wodecka)生活在一起,没有经历波兰1989年发生的巨变,直到2002年才返回克拉科夫。他回忆说:“我在巴黎的第一年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年。我几乎感到羞愧。我的国家是如此灰暗,我的一些朋友在监狱里。我当时爱上了玛雅。我没有工作。我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游荡。我拥有这种自由——因为我不属于它。”流亡的特权构成了波兰诗歌传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十九世纪最好的波兰作家都住在巴黎,当时人们觉得,作为一个被迫的局外人,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对国内的情况有更好的看法。而在战后伟大的波兰诗人中,米沃什和赫贝特都在巴黎居住了多年,似乎翻新了波兰文学的神秘性。但扎加耶夫斯基虽然流落在外,却想抵制这种神话化。“我知道,波兰人很适合扮演流亡者的角色,这是波兰的传统。我们的基因是,一旦你到了巴黎,你就不会绝望”,因为走过巴黎,你将看到“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写了这个,而肖邦(Frédéric Chopin)住在这里”。扎加耶夫斯基说:“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戏剧化。我试图保持正确的比例。”某次诗歌朗诵会上,他被介绍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马上反驳:“对不起,这是不正确的,我是一个色情的流亡者。”
从波兰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巴黎的流浪者,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看待他的新世界,偶尔也会有一阵欣喜若狂的顿悟。虽然写诗很早,但或许可以说,扎加耶夫斯基只有到了八十年代,才发现了自己的诗歌习惯,意识到早先自己不过是在借用诗歌语言。当我们在八十年代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时,你不可能把它误认为是其他人的。在七十年代,诗歌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在八十年代,诗歌是他的呼吸、他的脾气、他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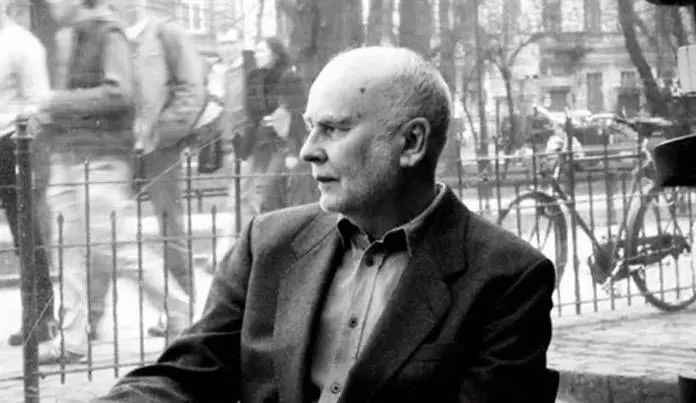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通常从一个图像或思想冲向下一个图像或思想,形成一个不连贯的整体,但又能感觉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像通过火车窗瞥见的风景。他的诗是故意充满希望的——拥有一个必须努力保持乐观的人的乐观。在《自由》(Freedom, 1982)一诗中他写道:
但即使在我不知如何定义
自由的本质的时候
我也清楚地知道
被囚的意味。
在一首富于个人特色的诗中,他形容说,当他思考朋友对世界的冷酷无情的看法时,太阳从云层后面冒了出来,他“被幸福的锋利倒刺刺穿”;这首诗是对一位住在巴黎的波兰移民画家的忧郁的回应。他在诗集《永恒的敌人》(Eternal Enemies: Poems,2008)中宣称,诗歌“寻找光辉”;更确切地说,他自己总在寻找它。“上帝,给我们一个漫长的冬天/和安静的音乐”,他在深情的诗《火焰》(A Flame)中写道:“给我们惊讶/和火焰,高高的,明亮的。”
《火焰》出自扎加耶夫斯基2002年出版的《无尽:新诗选》(Without End: New and Selected Poems),而“不要让清醒的时刻消溶”(Don’t allow the lucid moment to dissolve),是诗选中收录的一首诗的标题,也许可以恰当地形容扎加耶夫斯基所有的诗歌努力: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从历史的重压中拯救出来。或者,正如他在“9·11”袭击事件后一周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首诗所表达的(尽管这首诗的写作远在这一悲剧性事件发生之前),“试着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Try to praise the mutilated world, 2001),这首诗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在这首诗中,他要求我们既要看到世界的悲剧,也要看到世界的永恒之美: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在评论这首诗时,他强调它诞生于情感的冲突,诞生于两种确定性的并置:“第一个是我对自己的确认,这是我多年来寻求对内心立场的理解后所达到的,我确信自己是一个赞美者,而不是一个激进的反叛者(即便一开始我是站在反叛者一边的)。第二个是观察到……我想要赞美的这个世界已经严重腐败、残缺不全,充满了绝望和失落。它激发了我的想象力。矛盾是美丽的。”
在支离破碎和不完美的生活中,将启示的闪光延伸为持久的真理,是扎加耶夫斯基在其诗歌写作中唤起的不可能的梦想。
02
在中间:于现实和超验间行走
虽说如此,扎加耶夫斯基对诗歌也充满了戒备。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提到所谓“诗意的栖居”,但诗意,其实是需要警惕的。诗歌一直自认为是对世界进行判断、自我陶醉和自行公义的领地,所以雪莱(Percy Shelley)才会说,诗人是世界的最终立法者。
在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看来,诗人的思维与极权同构,二者都蔑视凡庸的生活,追求崇高的人生意义,这些意义对他们来说是确凿无疑的。昆德拉把斯大林恐怖时代的特性描绘为“刽子手和诗人的联合统治”,也就是说,极权主义只有在刽子手的谋杀本能可以被诗人转化为神话和神秘主义的地方才能生存。
从批判极权的角度出发,昆德拉解构崇高,在作品中常常运用反讽来消解政治、爱情等价值。他的矛头犀利地指向人们习惯于极度肯定的社会和给出答案的世界的那种愚蠢。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Life Is Elsewhere,1973),原名叫做《抒情时代》,是对诗歌的某种最苛刻的否定。他说道,当诗人们无力发起突破现实的行动时,所采取的对付方法,便是抒情态度。诗由此成为现实行为失败的补偿证明。
可是,如果怀疑过了头,便会走向绝望。昆德拉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假如你意识到周围的世界不值得认真对待,疯狂的后果便会出现。”捍卫诗歌的扎加耶夫斯基正是在此处看到了反讽的局限。他知道反讽可以成为反对消费主义、宗教、政治或任何需要被削弱的敌人的有力武器。但他也提醒人们注意反讽的危险性,因为反讽往往“掩盖了知识的贫困”,并且无法带来救赎。

米兰•昆德拉
反讽的对立面是激情。扎加耶夫斯基写了一篇雄文《为激情辩护》(In Defense of Ardor,2002),提到一个“在中间”的概念:
我们总是“在两者之间”,我们的不断运动总是以某种方式背叛另一方。沉浸在琐碎的生活中,沉浸在实际生活的平凡常规中,我们忘记了超越性。而在向神性靠拢的同时,我们又忽略了普通的、具体的、特定的东西。
这样的“在中间”可以用来定义“存在”:人永远处于现实和超验之间的行走状态。我们要登上高山,但也要回到厨房——所以,志在高山的人要从厨房做起,而身处厨房的人不要失却望山之志。扎加耶夫斯基更进一步指出:“向高处的征程应当在一种个人诚实的状态下进行。”
在这里,扎加耶夫斯基冒险抛开怀疑,同时保持无决断;他的诗在自信和不确定性之间巧妙地移动。通过抒情,他把眼前世界的碎片变成对日常的和神圣的一种负责任的理解。扎加耶夫斯基同时降低和提高他的视线,在盯着地板的时候也看见天堂。在他的标志性诗歌《转变》(Transformation,收入《无尽》,2002)中,扎加耶夫斯基直面他在《为激情辩护》中所批评的“无比反讽和怀疑的景观”,坚决依靠诗歌的转变潜力,而这是指导他的“一件事”。
诗中写道:几个月来,他没能写出“一首诗”,他“谦卑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平凡事物——报纸、鸟、日落和窗台,但只发现它们的“谜语”和“沉默”,而没有任何超越的杠杆。但十分突出地,诗人并没有从一个坚固的世界退缩,而是坚定不移地追求诗歌的古老圣杯——一缕可以瞥见的理解之光,如天上的火花,超越这个世界:
我走了很久
只渴望一件事:
闪电,
转变,
你。
“在中间”,让我们想起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扎加耶夫斯基说:“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经历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写下了一首诗歌之后,我们会去厨房,决定晚饭吃什么;然后我们会拆开附有电话账单的信封。我们将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明智的亚里士多德,否则等在上面的会是疯狂,等在下面的会是厌倦。”
生活,就是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明智的亚里士多德,避免疯狂与厌倦。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平凡的”,但“平凡的生活欲求着”。
平凡的生活
Ordinary Life,2007
我们的生活是平凡的,
我从丢在一把长椅上的
揉皱的报纸上读到。
我们的生活是平凡的,
哲学家告诉我。
生活,寻常的日子和忧虑,
音乐会,交谈,
在城市郊外的散步,
好消息,坏消息——
目标和思想
却未得完成,
如粗糙的草稿。
房子和树
欲求更多的事物,
在夏天,绿草地
覆盖这多火山的星球
如扔向大海的一件外套。
黑暗的电影院渴望光芒。
森林热烈地呼吸,
云团轻柔歌唱,
一只金色黄鹂祈求着雨。
平凡的生活欲求着。

03
矛盾是美丽的,而诗歌是有创意的妥协
扎加耶夫斯基通过连续的二分法和重建曾经被肢解或破坏的东西的需要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从来没有流亡,但也未曾定居。地点及其对立面——移位——塑造了他的生活,而他从不畏惧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位他的诗歌。在《为激情辩护》中他总结道:“从利沃夫到格利维采,从格利维采到克拉科夫,从克拉科夫到柏林(两年);然后到巴黎,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每年从那里到休斯敦四个月。然后返回克拉科夫。”从一个临时家园到另一个临时家园,从一个陌生的城市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是由他无法控制的必然性和历史环境决定的,但也是个人的选择。从他的散文集,如《双城:论流亡、历史和想象》(Two Cities: On Exile, History and the Imagination,1995),到诗集,如《震颤》(Tremor, 1985)、《初学者的神秘主义》(Mysticism for Beginners,1997)、《无尽》和《不对称》(Asymmetry,2018),以及他的回忆录《另一种美》(Another Beauty,2000),都不难体味他眼中的现代文明的悖论。
“你迈出的每一步/都会留下无法抹去的痕迹”,扎加耶夫斯基曾经写道。结果就是这些痕迹的累积映射,多重现实的压缩,其中一个永远不会取代另一个,但都存在于诗歌的单个时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扎加耶夫斯基在题为《公告》(Communiqué,1972)和《肉店》(Meat Shops,1975)的诗集中,毫不含糊地嘲笑了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一致和谎言。他是“68一代”的两个主要口号的作者——“说真话”和“直截了当”——这很好地说明了相关艺术家群体的雄心,想要无情地揭露存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教条的伪造品。扎加耶夫斯基在收入《公告》的诗“真相”(Truth)中写道:“说真话,这就是你服务的原因。”在“不要让清醒的时刻消溶”一诗中,他呼吁:“不要让清醒的时刻消溶在坚硬干燥的物质上/你必须铭刻真相。”因此,在新浪潮诗歌中没有相对主义的位置。相反,扎加耶夫斯基提出了一种将伦理与美学联系起来的新现实主义。
然而,关心现实的扎加耶夫斯基深知事情的另一面:诗歌创作必须拥抱而不是躲避矛盾。正如他以《多元颂》(Ode to Plurality,收入《震颤》)来回应波兰的戒严时所说的:“一首诗在矛盾中成长/但它无法超越矛盾。”在八十年代,扎加耶夫斯基是最早定义打破文学与政治之间紧密联系的必要性的作家之一,因为艺术的目标比政治更重要,或者说,艺术无论如何不同于那些对政治动荡作出反应的喧闹的公共或政治新闻。在《双城》中,他提出,文学有两个缺陷:其一是,作家只专注于他自己——他自己的弱点和自己的生活,而忘记了客观世界,忘记了对真理的追求;其二则反之,即作者只专注于世界的真相——客观现实、正义,对人、道德和习俗的评判。

一位诗人如何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取得平衡?扎加耶夫斯基认为,诗人就像哲学家一样,也必须以一种离散的方式讲述他的生活。“有时我认为诗歌处于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的中心,而所提到的两个缺陷只是矛盾的一例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诗歌是矛盾之间的一种妥协——但却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妥协。”
波兰人似乎既哲思又充满激情,而扎加耶夫斯基惯用诗人的眼睛和哲学家的思想来描写世界和人类的状况。他并重现实的本质和视觉表象,在诗集《未看见的手》(Unseen Hand, 2009)中告诉我们,同时关注具体和抽象是至关重要的。他喜欢运动的视角和整体的视角。对他来说,宇宙是一张符号地图,引导我们走向隐藏的意义。当意识掌握整体性,意义是在罕见的顿悟时刻被发现的,而且,不需要成为神秘主义者也能从平凡的经历中获得顿悟。
扎加耶夫斯基渴望思想家和诗人的安全陪伴,有一个问题牢牢吸引着他,即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每个诗人和哲学家都有站在这两种主要力量之间的感觉。但这绝对是我的情况,而且似乎每年我都更加意识到这一点。我无能为力;我只是试图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受到智力生活的两个相反极的诱惑意味着什么?”
按照他的说法,哲学提出了公开的批判性问题,而诗歌仅暗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哲学性的。它试图捕捉存在本身,但以一种反复无常的方式。捕捉行动中的存在,而不是用学术的方式来定义它,是诗人雄心的一部分。
诗歌不论证,但并不等于它可以与思考隔绝。而思考总是进入矛盾的领域。所以,扎加耶夫斯基主张,诗歌应该与思维领域也即矛盾领域建立一种有意识的关系。“从那里开始,诗歌就有了一些东西,一些补充——法国人称之为supplement d’ame,灵魂的补充。”
沿着这些关于矛盾的思考,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中不时出现的一个主题涉及狂喜和反讽的矛盾元素。它对应于非常古老的理性与启示之间的斗争或紧张关系。“两种矛盾的元素在诗歌中相遇:狂喜和反讽”,他在《双城》中断言:“狂喜的元素与无条件接受世界联系在一起,包括残酷和荒谬的世界。相比之下,反讽是思想、批评和怀疑的艺术表现。”他权衡这两个因素,但他最广泛的冲动是试图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事实上,也就是赞美世界本身的神秘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朝圣者,一个探索者,一个寻找神圣、不变和绝对的庆祝者。他的诗充满了光辉灿烂的时刻。它们是精神的象征、未知的赞歌、超越的杠杆。文学翻译家兼剧作家菲利普·博姆(Philip Boehm)惊叹说,这些诗“将我们从任何可能使我们感觉迟钝的日常生活中拖拽出来,从任何可能使我们陷入简单存在的事物中拖拽出来”。
当他这一代的其他作家转向阴郁怪诞或辛辣讽刺时,扎加耶夫斯基回到了哲学,并逐渐凭借安静的坚韧,治愈了自己的反讽,诗人在《漫长的下午》(Long Afternoons,收入《初学者的神秘主义》)中称其为“看到但无法穿透的凝视”。
04
热爱二元性:玩弄悲伤,调情绝望
《为激情辩护》里有这么一句:“在充满反讽和怀疑的世界里停留太久,会唤醒我们对不同的、更有营养的食物的渴望。”扎加耶夫斯基仍然相信诗歌应当提供“有营养的食物”,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2004年在《卫报》评论道:“在扎加耶夫斯基最好的诗歌中,他成功地将想象空间与经验联系起来;所见、所闻、所记的一切事物,无论是悲伤还是喜悦,对他来说都具有与魔法一样的力量。”
魔法需要通过技巧来展示。作为一个技艺精湛的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善用雅努斯修辞,把诗歌中固有的矛盾体现出来。雅努斯(Janus)是罗马的两面神,掌管开始和结束、早晨和晚上、过去和未来。他是一位“门槛”之神,同时看到两个方向——门内和门外。写诗时,扎加耶夫斯基经常戴上雅努斯面具,试图用语言捕捉一种双重视角,一种对立统一的幻想时刻。通常,这种策略涉及情绪或态度的混合,还有不同情绪或观察的丰富组合。

雅努斯
比如,“气味是春天,气味是悲伤”;“我看到树林里的叶子被霜冻焦了”; “有时候,缩减就像周日面包的面团一样膨胀”;当然还有,“歌唱的就是沉默的”。“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收入《未看见的手》)一诗的结论是:
比较白天和黑夜;就是这样。
梦与醒,世界与心灵。喜悦。
沉着、专注、心的漂浮。
明亮的思绪在黑暗的墙壁里闷烧。
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什么。
我们生活在深渊里。在黑暗的水域中。在光亮上。
在《熔岩》[Lava,收入《画布》(Canvas, 1990)]中,诗人呈现了一种明确的来回运动,强调了现实的最终不可知和意义的无尽推拉本质:
如果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
都是对的
两个世界并存,
一个平静,另一个疯狂;一支箭
不假思索地冲刺,另一个,任性,
旁观;同样的波浪移动又静止。
动物们突然来到这个世界上
又离开,白桦树叶在风中翩翩起舞
当它们在残酷、锈色的火焰中分崩离析。
熔岩摧毁又保存,心脏跳动
又被敲打;出现战争,然后又消失;
犹太人死了,犹太人还活着,城市被夷为平地,
城市长存,爱情消逝,亲吻永恒,
鹰的翅膀必须是棕色的,
尽管我们已不复存在,你仍与我同在,
船沉,沙在歌唱,云在飘荡
就像破烂的婚纱。
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中还有许多其他看似矛盾的二元性,他玩弄悲伤,调情绝望。尽管他写道,“诗人伸手拿起羽毛笔:/他今天会温柔,还是愤怒?” (“历史小说”,收入《画布》),他最常选择这些现实之间的鸿沟。“我们存在于元素之间,/火与睡眠之间”(“蝉”,收入《初学者的神秘主义》)。
终其一生,扎加耶夫斯基一直是一位具有引人注目的二元论的诗人(他宣称:“世界是撕裂的。热爱二元性!”另一处,他断言,“诗人是一个天生的中间派”)。在他的作品中,现实与想象、历史与当下、暂时与永恒之间存在着强大的辩证法。
这其实就是济慈(John Keats)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概念——“能够处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而不会急躁地追求事实和理性”——还有他自持的双重心态:同时生活在黑暗的水域中和明亮的光线上。
扎加耶夫斯基这样描绘诗歌创作的过程:
《写诗》
(Writing Poems,2009)
六月的炙热,
写诗是一场决斗
没有人赢——一方面
一个阴影升起,从蝴蝶的角度来看
巨大如山脉,另一方面,
只短暂瞥见光亮,
形象和思想就像火柴的火焰
在冬天痛苦降临的夜晚。
一方面,巨大的山脉暗示着宏伟的哲学层面(讽刺的是,它是由蝴蝶看到的);另一方面,在一个相当凄凉的夜晚,一丝顿悟的火花跃然而出。两者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共同存在。这种二元性赋予了诗歌以力量。扎加耶夫斯基称他所发现的为“短暂瞥见光亮”,尽管读完他的诗,人们可能会争辩说,这些“一瞥”必然比暂时缓解黑暗和寒冷的“火柴的火焰”持续得更久。
05
真正的生活不存在,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扎加耶夫斯基谴责任何东西,那就是浅薄而狭隘的诗歌。他在《反对诗歌》(Against Poetry,2004)一文中写道:“当代大众文化虽然具有娱乐性,有时也无伤大雅,但其特点是对内心生活的完全无知。它不但不能创造这样的生活,反而消耗它、腐蚀它、破坏它。”诗人的角色是捍卫和滋养内心生活;静坐并与内心的声音交流,这是“我们自由的基础”。
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中,残酷与幽默、乐观和对自然的敏锐欣赏交织在一起。“好吧,为什么不呢”,他说。 “你写一首诗。你还活着。你不想成为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我认为,当你写诗时,你渴望得到比简单的哀叹更大、更整体的东西。在诗歌中,我认为你试图重建人性。人性总是哭与笑的混合体。”
扎加耶夫斯基以一种可以被称为“杂耍”的方式描绘这种混合。例如,《在一家美国酒店的房间里观看<浩劫>》(Watching Shoah in a Hotel Room in America,收入《画布》),将三种不同的意象、环境和体验同时悬浮在空中,就好似杂技演员手中的三个杂耍球:
在一家美国酒店的房间里观看《浩劫》
有些夜晚像小马驹的皮毛一样柔软
但我们更喜欢下棋或打牌。这里,
一些酒店客人唱着“生日快乐”
在独眼电视漫不经心地变换图像时。
我童年的树已经跨越了海洋
从屏幕上冷静地跟我打招呼。
在神学争论中,波兰农民充满耶稣会热情
只有犹太人保持沉默,
因漫长的死亡而疲惫不堪。
我青春时航行的河流
小心翼翼地流过遥远而陌生的大陆。
干草车拉的不是干草,而是头发,
它们的车轴在羽毛般的重量下吱吱作响。
松树宣称,我们是无辜的。
党卫军军官们都憔悴而苍老,
医生们努力挽救他们的心脏、生命和良心。
已经很晚了,睡意袭来。
我想睡去,但我的邻居
合唱团的“生日快乐”声音更大:
比垂死的犹太人还大声。
巨大的卡车从苍穹中运送星星,
阴沉的火车在雨中驶过。
莫扎特忏悔,我是无辜的;
只有白杨像往常一样颤抖,
准备承认自己的所有罪行。
捷克犹太人唱国歌:“哪里是我的家……”
没有家,房屋着火,冰冷的煤气在里面呼啸。
我变得越来越天真、越来越困。
电视让我放心:我们俩
是无可怀疑的。
生日变得更热闹。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鞋子,堆成塔
高如天,微弱地叹息:
唉,现在我们比人类活得更久了
让我们睡吧,睡吧:
我们无处可去。
第一个“杂耍球”(来自诗中暗指的时刻的意象)表现为“一些酒店客人唱着“生日快乐”/独眼电视漫不经心地变换图像”等诗句。第二个球(来自诗人在波兰的童年时代的意象)出现在诸如“我童年的树已经跨越了海洋/我青春时航行的河流”之类的诗行中。第三个(受害者和苦难的各种例子)在诸如“干草车拉的不是干草,而是头发/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鞋子,堆成塔/松树宣称,我们是无辜的/党卫军军官们都憔悴而苍老”等的诗句中表现得惊心动魄。通过在整首诗中杂耍三个“球”,扎加耶夫斯基模糊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像杂耍表演中的球在视觉上无法区分,而在物理上却是分开的一样。人们知道空中有三个单独的球,但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很难区分哪个是哪个,更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在任何一个球上。
这样的杂耍,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凸显真正的恐怖——它的确是一首恐怖诗——读者感受到的恐怖,不仅来自于大屠杀事件,来自于诗人所看到的纪录片本身,还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不断侵扰,这些侵扰不允许纪念或哀悼。它们不断闯入。隔壁房间里的《生日快乐》歌手反复挤压观看者的意识,更不用说睡眠本身了,所有这些都在降低对世界苦难的认识。如果说生命被唤回是一种慰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则是苦乐参半了。
扎加耶夫斯基相信,万事万物都是复杂的。“我们有轻浮的部分,我们幸存下来,只是有时滑过。尤其是当你写诗时,你必须有那些深深哀悼的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你为别人工作。他们唱‘生日快乐’,是因为你做了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分工。”
这让我想到了辛波斯卡的诗《现实的要求》(Reality Demands),它的观点是即使在悲剧之中,生活仍在某个地方继续进行。扎加耶夫斯基对“永远不会再发生”或“永远不会忘记”的保证表示怀疑。他以低调而严谨的方式暗示,人类的记忆被一种固有的平淡无奇的脆弱所污染。空喊口号无法纠正道德想象力的缺失。

扎加耶夫斯基最后出版的一本诗集题为《真实生活》(True Life,2023),题词来自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真正的生活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个转折传达了重要的意义。没有真正的生活,没有理想的生活,没有关于生活的想法,只有世界本身及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和狂喜。他用一首关于勘误的诗结束了这本最后的诗集:
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生活
以免需要勘误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否可能
勘误表是否真的可以没有错误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