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儿童与成人界限的消失;男人与女人界限的消失;英雄与凡人的融合;工作与休闲的模糊化——我们都是越界人,活在时代更替的夹缝中。这个越界的经验,是世界上无数受技术与媒体影响、身份含混模糊、经历生活与工作流动、感受代际震荡的群体与个人的共有经历。
关键词:界限 越界人 夹缝
3 英雄和凡人的融合
梅罗维茨所分析的第三种现象,即政治英雄与普通市民的等同,也是由电视肇其端的。这在大卫·哈伯斯塔姆所著的《掌权者:美国新闻王国内幕》一书中,有着生动的描述:
在德克萨斯州的约翰逊城,一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为林登·约翰逊的电视回忆录进行采访。……“你们这些家伙,”他脱口而出,“你们这些新闻界的家伙。正是因为你们,政治已变得面目全非。你们破坏了我们国会成员和城市机构之间的全部联系和机能。你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些陌生的人。”……“除了你们之外任何机器都无法创造出一个特迪·肯尼迪。他们全是你们的,你们的产品。”
梅罗维茨说,在社会上没有充斥电视之前,政治领袖们被当做一种“神秘的存在”,遥处普通公民之上,很容易控制有关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做了什么的信息。然而,电视改变了一切。一方面,如果不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政治领导人对公众的吸引力就会缩水;但是如果过度曝光,他们就会彻底失却这种力量。这是因为过度曝光会减少领导人的神秘感,使他们成为凡夫俗子。由于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信息的即时性,普通公民现在得以仔细打量和检查其领导人的形象及言辞。这就是梅罗维茨所言的双刃剑:电子媒介给政治权威展示自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舞台,但同时这些权威也失去了印刷环境下神秘的光环,因为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具体的人。而一旦政治权威的形象距离与普通人接近起来,任何完美就不复存在了。
波兹曼指出,电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更亲密,更个人化和更富有表现力。印刷媒介展示了经过修饰的有风格的讯息,而电子媒介则展示了自发的和“自然”的讯息。其实这个“自然”是打引号的,因为电视带给我们的是高度包装。波兹曼痛斥说,为了包装自己,美国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甚至神父们,医生和律师们,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们,也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由此,政治新闻中的象征形式已经彻底改变了。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力从评估个人的政治主张,变成对政治人物形象直觉的、情绪化的评估。在更广泛的层面,人们对社会名流的评估也是如此,因为唯有直觉和情绪才是注意力的先决条件。“在我们的社会中,成功就意味着公众注意的认可,”克里斯托弗·拉什写道。这种认可的过程迅速而经常,基于真正成就上的真正的成功不再是获得公众注意的要件了。注意力的要求如此之高,连那些符合客观标准的衡量的成功人士都不断寻求更多的认可,例如,大亨们一反过去的隐遁,频频在媒体中出镜。如今,商业成功的标志是麦当娜式的知名加上盖茨式的富有。唐纳德·特朗普成为自我推销的CEO的典范。似乎,只要无人关注,所有的伟绩都会烟消云散。

在电视的脱口秀中,人们渴望暴露自己所有的一切,不和的家庭,受压抑的童年,婚姻,婚外情,性创伤,把电视变成了杂耍和论坛的混合物。这造就了查尔斯·德伯所称的“名人的民主化”,即普通人可以通过把自己的错误、罪行、创伤和悲剧等等公之于众而获得巨大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名人杂志刊登偷拍的明星卸妆照片,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名人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在自恋的时代,没有什么人会取得真正的成就。狄兰·伊文思在《卫报》上评论说:“现在,如果某个人的才能远胜于我们,我们不会祝贺他——我们羡慕他,但怨憎他的成功。似乎我们并不想要我们仰慕的英雄,而宁愿要我们可以认同的英雄。如果阿喀琉斯今天还在的话,所有的大字标题谈论的都会是他的脚踵。”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屌丝的逆袭,精英的倒掉,嘲弄经典的恶搞,是网民最乐于消费的快餐。有关马云的段子“永远不要忽视一个屌丝的决心和力量!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成为最新心灵励志鸡汤,原因是它完美地表达了草根对英雄的逆袭梦想。《新周刊》说得好:在网络文化里,要区分神圣与卑微、严肃与戏谑、伟大与渺小,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它们常常以彼此混杂、互相冒充的形式出现。

凡此种种的符码混合,在文化意义上,令雅俗的分野也土崩瓦解。有人说,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众的俗趣味对精英的雅趣味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布尔迪厄在谈论高尚品味对低俗品味的压倒时说:“对下层的、粗俗的、通俗的、唯利是图的、卑屈的、乐趣的否认,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它是建构了一个如此的文化神圣性,并包含了所谓的先知们对升华的、高雅的、无私的、免费的、显赫的、一点都不亵渎的、优越的美学自我满意的正确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不难理解俗趣味逆袭雅趣味成功时,大众所感觉到的那种瓦解“文化神圣性”所带来的的巨大的快感。
4 工厂与休闲的模糊化
当19世纪的思想家谈论进步的时候,主要是指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增加,两者都被视作进步的基本条件。进入20世纪,很多社会学家,如因《孤独的人群》而闻名的大卫·里斯曼,都坚信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的闲暇时光将极为充裕。他们甚至担心人们无法应付这些自由时间。
1967年,法国社会学家杜马斯蒂埃出版《迈向闲暇社会》,指出与19世纪中叶相比,工作时间已大为缩短。周工作时间从大约75小时(工作6天,每天13小时)减少到约45小时。杜马斯蒂埃认为,闲暇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它构成了“生活”的核心成分,与更大的课题如工作、家庭及政治等等具有深刻而微妙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课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框定。他是最早在学术框架下研究闲暇的学者之一。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1993年,美国社会学家朱丽叶特·肖尔出版《工作过度的美国人:闲暇的意外衰减》,该书的副题显示,闲暇并没有像社会学家预计得那样如期到来。相反,过去20年中,闲暇在减少,而工作时间在增加。需要注意的是,肖尔这里所说的工作是付酬工作与不付酬的家庭劳动的总和。
虽然工薪阶层的收入增加了,但他们为此付出了时间。到90年代末,已婚并育有子女的双职工一年新增的工作时间达151个小时。肖尔形容说,这就好像是工业革命重返美国。2001年的一项哈里斯测验表明,美国人的周工作时间(包括家务劳动和受教育)由1973的41小时上升到50小时,同时,闲暇时间由26小时下降到20小时。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界关心的话题从“闲暇的丰足”转变为“时间的匮乏”。时间压力导致的紧张、慢性疲劳等问题吸引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在《新闻周刊》1995年的一项调查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声称自己“身心俱疲”。
人们一度对工作时间的起始与终止有明确的意识,但高科技的出现打破了工作与闲暇的界限。传真机、计算机和手机的发明使人们更易于把工作带回家,闲暇时间也被这些现代技术手段切割得支离破碎。闲暇现在由“偷来的片刻”组成,社会学家称之为夹在各种活动之间的“时间三明治”。当人们成为过度工作的牺牲品,其闲暇时间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长时间的工作损害了闲暇,减少了闲暇对人们的吸引力,从而使他们更加倾向或屈从于长时间的工作。
总体来看,闲暇时间的减少存在两大原因:第一,工作成为现代宗教,人们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来界定自身。第二,新消费主义盛行,对物质的欲望似乎永无止境。
从第一点原因来看,工作变成新式消遣,构成了一个普遍趋势。2003年11月,联邦快递公司发布的全美调查表明,10%的被调查者拥有自己的企业,三分之二的人梦想拥有自己的企业,而最令人震惊的是,高达55%的人声称,如果他们能够筹到资金,将会离开目前的职位而自行创业。40%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创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从事自己热爱和激赏的工作”。
人们曾经把工作当作苦役,而把业余时间的个人爱好当作乐趣。而现在,工作就是乐趣之所在。工作就像是一种新的宗教,工作伦理则像一种新的道德。
成年人用在工作、找工作或者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上的时间最多。这是因为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工薪阶层挣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1年, 近2000万员工把部分本职工作带回家中完成,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他们一周平均在家里额外工作7个小时。而与工薪阶层相比,自由职业者工作的时间更长。然而,个体经营者或希望自己当自己老板的人群在迅速地增长。
而所谓的新消费主义的最大特点是:人们从就近比较到上下比较——不再用同等经济地位的群体、而是用收入水平最高的20%的人群作为参照物,来界定自己对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期望值。此前,较为普遍的目标是获得舒适而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现在,人们对致富和奢华有更为迫切的追求。20年前的奢侈品现在成为了必需品:更新潮的家用电器,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车,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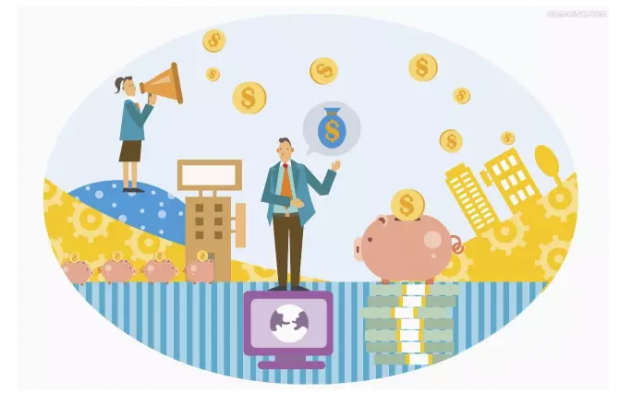
推动这股新消费主义的有三种力量:首先,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财富越来越多地聚集到20%的人口中。这种财富的向上分配使处于社会-经济金字塔尖的少数人得以大肆张扬自己的消费模式,因此影响了剩余的80%的人口的消费观念。
其次,从90年代开始,商业化的媒体出现了一个明显倾向,即把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文化典范宣贯给普通受众,社会大众的消费欲望脱离了社会现实,强有力地为电视、电影、报刊上的名流和虚构人物所引导。
第三,女权主义运动带来了女性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以美国为例,1950年代美国婚后女性就业率仅为11%。经历了60~7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而出现的的女权运动高潮后,1978年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上升到50%,1997年达到61%。在21世纪初头几年的经济繁荣期时,已婚女性就业率曾经回落到54%,但在2008年底金融海啸爆发后,因为生活压力增大所迫,美国已婚女性就业率重新上扬,在2010年上升到69%左右。随着中产阶层的妇女越来越多地进入层级制机构中工作,与拥有更高经济地位的人有了更为频繁的接触,她们更容易接受这些人所传递的消费信号。
工作与闲暇的此长彼消也反映在工作场所与家庭的空间关系流变上。家庭与工作场所的人为割裂与区隔,是工业革命给家庭生活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对在自家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和在家庭小作坊劳作的人们来说,不存在上班的概念。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大工厂、专业分工与城市化,彻底改变了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人们必须离开家庭,进入一个被“监视”的工作场所进行工作。这改变了农业社会的旧的时间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界节奏让位于以钟表的发明为标志的机械时间观,工人的工作时间被精确到小时、分、秒,几班倒的做法也出现了。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描述了早期现代时间感的变化,所有社会活动甚至人们的内在时间都与工业生产的节奏相匹配。
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互联网、移动通讯和宽带设施的发展导致了工作地点的重新安置,在这一过程中重塑了工作的特性。这方面出现的四个重要变化是:在家远程工作的上升;移动工作的增加;知识工作在城市中心及其高科技“集群地”的汇聚;国际性劳动分工的形成。对这些变化,有的人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例如,在以写作《虚拟社区》而知名的霍华德·莱因戈德的笔下,到处都是田园般的“电子小屋”,远程工作的专业人士充分享受高科技的好处,摆脱了每天上下班的烦恼,保持了和家人的接触,在工作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可以拿到传统工作地点以外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类:一是重复性的、低技术的数据输入和文案工作,二是高度复杂的“符号分析”工作如撰写报告等等。从事前一种工作的人收入不高,没有福利,也很少受法律保护,不会享受到传统工作场所提供的社会关系、培训、个人晋升。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生活在惬意的“电子小屋”中,不如说是在高科技的“血汗工厂”里挥汗如雨。
与之相对照,从事后一类的专业人士往往受过完备的教育、能够自我做主,在远程工作中享有相当程度的创造性,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归根结底,这些人和前一类人也不能被完全区分开来,两者都面临着工作/生活的平衡问题。在家工作加重了劳动负担,因为“在家”,所以需要同时承担工作与家务的双重负担;同时,原本可以全身心放松的下班时间,也因为工作进入了家庭而延长了实际工作的时数,使人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之中。个人如果缺乏良好的时间管理和自律能力,往往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虽然信息技术一直被指可以促进知识工作者在工作和生活间达成平衡,但现实情况却是,远程工作者所感受到的压力与挫折感与日俱增。这源于通信和信息技术所导致的不间断的生产,人们现在拥有了“24/7”的时间观。乔纳森·柯拉瑞精彩的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分析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无休止的需求。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清醒和睡眠的界限正在被侵蚀,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其他重要界限的消失,比如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闲。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在线娱乐和网上购物的流行、无处不在的视频对注意力的吸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进入了一种无眠状态,从而令人类生活进入一种普遍性的无间断状态中,受持续运作的原则支配。不限时间地点的网上工作本来被看作是一种自由,现在却被发现只是一种新的奴役机制。
5 我们都是越界人
在我们这个技术不断被开发、消费不断被升级和人性不断被开采的世界中,一些人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我想借用“liminality”一词来说明当下的生活境况。
“liminality ”取自拉丁文的 limen,本是threshold (门槛)之意。在人类学范畴里,首先是研究民俗学的法国学者阿诺德·范·杰内普在20世纪初经由对不同种族文化的仪式的共同观察,提出一个典型的“人生经历仪式”(rite of passage,也称)包含三个部分:1)Rite of separation(分离仪式),同本来的身份/群体相分离;2)Rite of transition(过渡仪式),位处过渡,或许格格不入;3)Rite of incorporation(融合仪式),投入新的身份/群体。杰内普用了“limen”一词作为通过仪式的中心观念。因此,过渡的仪式称liminal rites,分离的仪式称pre-liminal rites,最后阶段的融入仪式称post-liminal rites。中文可分别译为越界前仪式,越界仪式,及越界后仪式。
对于重大界限消失后的生活,“liminality”表达了不前不后的中间段落。在这个段落里,人脱离了原来的身份,又未曾达至完成新身份,是身份、角色、自我意识、对外关系都难以确定的尴尬时刻。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把过渡时期的处境归纳为“离开身份系统”,人在这时不属于任何身份类别之内;原属不同阶段及身份的各人,在越界处境中彼此都拉平了,大家变得无所依恃,过去显示所属身份/地位的饰物都被脱去,人好像成了无名氏。
我们都是越界人(liminal people),活在时代更替的夹缝中。这个越界的经验,是世界上无数受技术与媒体影响、身份含混模糊、经历生活与工作流动、感受代际震荡的群体与个人的共有经历。对这个经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学叙述,来承载和容纳其间的模糊性、失序性与无所适从性。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许多问题,笔者并没有答案。界限的模糊化造成了一种“晕眩”感,原本历历分明的世界,现在,在一种缺乏历史性与时间感的境况下,变得因无法驻足凝视而统统化作一闪而过的模糊光影。晕眩,是夹缝中生存的基本感受。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