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抑郁的感觉时,读到琼·狄迪恩的。当时听说她是美国在世的最好的散文家,她一直坚持认为,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除非把它写下来。我把能找到的她的著作都翻检了一遍,我发现,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写下自己的生活。

琼·狄迪恩,美国随笔作家与小说家
作为前记者,我难免对她的“新新闻主义”生涯感到好奇;作为学文学出身的学生,我也读了她的小说。她的非虚构写作毁誉参半。“她的才华在于写出了文化的情绪”,作家凯蒂·罗伊夫在一次采访中说。“她通过自己高度特立独行和个人化的写作,成功地引导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精神。她与这个时代完美匹配,略带偏执、略带歇斯底里、有一种高亢的敏感。这是一个作家与时代的完美结合。”
批评者则认为,狄迪恩的写作中满是有关自身的不正常情绪,评论家约翰·拉尔写道:“她沉思于她的荒凉,并使之变得优雅。”作为一个记者,她显然有不合格之处:“狄迪恩被派去了解一个民族的脉搏,最后却为自己量体温。”芭芭拉·格里祖蒂·哈里森甚至称狄迪恩的风格是“一袋花招”,“主题总是她自己”。
这些批评倒也不是全无道理。狄迪恩采访所到之处,似乎都可以发现相同的情势:迫在眉睫的混乱,充满恐惧的气氛,以及不知情的参与者用陈词滥调描画的荒谬。她似乎总是在一场可怕的灾难边缘写作,以至于她唯一可用的反应是退回到一种自闭症。
狄迪恩并不避讳自己的心理波荡。在她的第二本散文集《白色相簿》中,她把当时进行的一次心理评估的摘录包括在内。“罗夏测试记录被解释为描述了一个正在恶化的人格,有大量防御失败的迹象。”记录进一步指出:“在她看来,她生活在一个由奇怪的、冲突的、难以理解的、尤其是狡猾的动机所驱动的世界中,这些动机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和失败。”这样的描述,可以直接用来诊断狄迪恩小说中的典型女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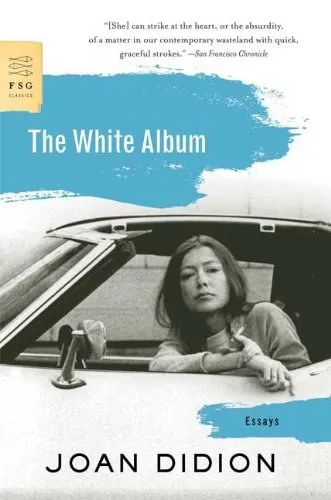
狄迪恩散文集《白色相簿》
角谷美智子认为她笔下所谓“狄迪恩的女人”是“个人荒原”的凄凉住客,时而沿着高速公路、时而穿越国家边境四处游荡着,努力抹去意识的痛苦。狄迪恩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的关注点几乎如出一辙——暴力、恐惧、令人作呕的世界失控感——仿佛她总是被麻烦之事、瓦解的人格和刚刚肇始的混乱很自然地吸引过去。
这些“狄迪恩的女人”们疏离、聪明但难以捉摸,通常总是宿命论的。而且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女主角都有一个麻烦的女儿。这样的阅读把我直接带到了狄迪恩2011年的回忆录《蓝夜》,触及她女儿昆塔纳的病痛与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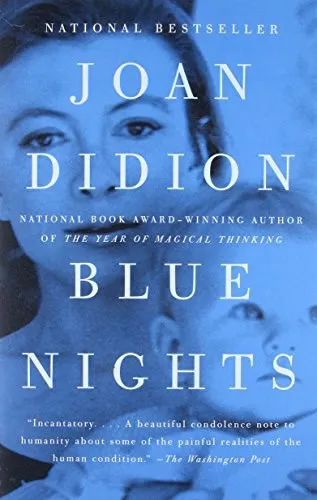
狄迪恩回忆录《蓝夜》
在剖析了别人的痛苦几十年之后,狄迪恩在过去十几年里把手术刀转向了自己。“作家总是在出卖别人”,她在第一本散文集即1968年的《向伯利恒跋涉》的开头写道。可是,如果说她在《蓝夜》中出卖了谁,那就是她自己。
在《蓝夜》中自我解剖时,狄迪恩似乎无法决定,她作为母亲是过于溺爱——“我一直把她当做一个玩偶来抚养”,还是过于冷漠——“我们是否要求她成为成年人?”她确实有一次向长大了的女儿提问,自己的养育是否有问题。女儿让她放心,算是放心吧。“我认为你们是好父母,但也许有点远。”
《蓝夜》讲述了许多事情:精神疾病、命运和我们对医疗技术的过度信任。但最重要的是狄迪恩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缺点的反思。昆塔纳在狄迪恩记叙丈夫逝世前后时光的《奇想之年》出版前六周去世,在经历了生活的痛苦(精神疾患、酗酒)和一系列连环病(肺炎、败血症休克、肺栓塞、脑出血)后,情感上的困难加剧了她的病情,狄迪恩想弄清她是否负有部分责任。“我认为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个好家长,或者,如果人们认为他们是好父母,他们应该再想想。”
在《蓝夜》中,女儿被截断的、麻烦的生活与狄迪恩自己的身体衰退交织在一起。她解释说,书名来自于初夏时节北纬地区的那些黄昏,给人一种阴森的印象,即黑暗可能永远不会到来。“我发现我的思绪越来越多地转向疾病,转向承诺的结束,日子的减少,褪色的不可免,光明的消逝。蓝色的夜晚与光明的消逝相反,但它们也是它的警告。”

狄迪恩与丈夫和女儿在一起
与《蓝夜》相比,《奇想之年》是一个更容易下笔的题目。当你有一个伙伴,一个你深爱的人,他和你同龄,有相同的参照系,你们在一起几十年,你会真的做到了解对方。而你的孩子,却永远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被理解。
所以,《蓝夜》真正写的,反而是狄迪安自己的某种传记,而且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传记。在书的最后,长大了的女儿仍然是个谜,而狄迪恩则是被揭示的那个女人。她所有的恐惧都在其中,她所有作品中的核心矛盾也暴露无遗:对不知道的恐惧与知道了以后的恐怖交织在一起。
在《蓝夜》中,狄迪恩如此谈论恐惧:
“当我开始写这些页时,我相信它们的主题是孩子,我们拥有的孩子和我们希望拥有的孩子,我们所依靠的让孩子依靠我们的方式,我们鼓励他们继续做孩子的方式,他们让我们一无所知、比对他们最随便的熟人都更无从了解的方式;我们对他们来说同样不透明的方式。我们对彼此的投资仍然过于沉重,无法看清对方。我们和他们都不忍心去考虑对方的死亡、疾病甚至衰老。随着书的推进,我突然想到,实际的主题毕竟不是孩子,至少不是孩子本身,至少不是作为孩子的孩子:实际的主题是拒绝参与思考,不能面对衰老、疾病、死亡的确定性,是一种恐惧。我一边往下写一边才明白,这两个主题是一样的。
当我们谈论死亡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我们的孩子。一旦她出生,我就从来没有不害怕过。我害怕游泳池、高压线、水槽下的碱液、药柜里的阿司匹林,以及“破碎之人”(此处指狄迪恩女儿脑中常年出现的一个幻象)本人。我害怕响尾蛇、激流、滑坡、出现在门口的陌生人、不明原因的发烧、没有操作员的电梯和空荡荡的酒店走廊。恐惧的来源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可能降临到她身上的伤害。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事实上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方,恐惧会消失吗?我们两个人的恐惧会消失吗,还是只有我的恐惧会消失?”
读到这里,我恍然彻悟,琼·狄迪恩的作品的秘密主题一直是她那麻烦的女儿。她并非在向伯利恒跋涉,而是在向昆塔纳跋涉。

狄迪恩与女儿昆塔纳
在《蓝夜》中,她禁不住问自己:“我是问题吗?我总是问题吗?”父母是那么渴望得到孩子的关注,他们全都是。狄迪恩一向以酷和时髦著称,但在冷静的外表下,我怀疑她比她自称的要虚弱得多。
在临终前数年,狄迪恩曾说:“我不再害怕,如果我曾经害怕过的话:我现在害怕的是不死。”2021年12月23日,狄迪恩去世,享年87岁。她留下了巨大的文学遗产,包括她对悲伤和失去的不可磨灭的叙说。《奇想之年》和《蓝夜》既奇特又熟悉,它给了我拯救自己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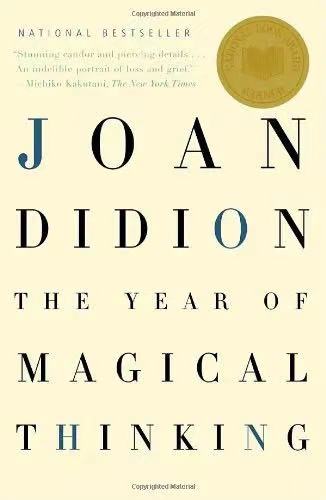
狄迪恩回忆录《奇想之年》
迪迪安写道:“我们是不完美的终有一死的人,即使在我们把必死性推开的时候也意识到它。”“当我们哀悼我们的所失时,我们也哀悼自己,无论是好是坏。我们哀悼自己曾经的样子。哀悼自己不再的样子。哀悼有一天我们什么也不是的样子。”
用别人无法企及的方式,狄迪恩书写了悲伤,她反对一个悲伤被完全隐藏的社会和家庭。然而《奇想之年》与《蓝夜》之间,还是有个很大的不同:失去配偶是人类经验的一个共同方面;失去孩子则不是。使《奇想之年》高于大多数有关悲伤的回忆录的,是狄迪恩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惊人能力,她一边向我们展示了失去的蛮力,一边又通过她的智慧将悲伤过滤,并将其塑造成一件艺术品。然而,孩子的死亡是无以复加的混乱,又有哪个作家能希望从中获得秩序?
难怪《蓝夜》写得支离破碎,当狄迪恩审视第二次痛苦的失去的时候,她的悲伤同时夹杂了对衰老和死亡的慨叹。《蓝夜》中那种告别式的感觉,是关于变老的。它是关于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身体上的屈辱,以及对无人照料的持久恐惧。

在狄迪恩关于加州的回忆录《我从哪里来》中,她描述了飞越东西海岸——那时她自己也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去处理她90岁的母亲的死亡。“现在谁来照顾我?”她问读者。“谁会记得我曾经的样子?”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所有人。总是如此。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